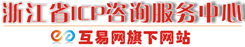研討會 | 孔祥俊:電子游戲保護的著作權與反不正當競爭路徑選擇
來源:電子商務法研究 時間:2025-05-09
一、應當盡快統一電子游戲的保護路徑
我最近一直關注電子游戲本身(含所謂的游戲玩法、規則以及畫面等)的保護問題。總體上看,司法實踐中電子游戲既既有整體性保護又有局部保護,始終在著作權與反不正當競爭保護之間徘徊,且有循環往復之勢,各地法院的認識和裁判始終有分歧。對于一個新出現的游戲類客體在保護歸類(法律涵攝)上有著作權與反不正當競爭之爭,經歷一個或長或短的嘗試和探索時期,這本身符合新客體納入知識產權保護的一般規律,像體育賽事直播畫面保護就曾經歷了類似的保護階段,數據權益保護正在處于這種階段。但是,像電子游戲保護歸類這樣的問題持續爭論了大約20年,迄今仍眾說不一,確實比較罕見。
法律適用雖然需要學術研究的支撐,學術研究仍可以眾說紛紜各抒己見,甚至可以觀點出奇和獨出心裁,但司法畢竟不同于學術研究,不能始終標準不一各自為政。我感覺雖然當前的各種說法或許均持之有據言之成理,但法律適用應當有統一標準,應當給權利保護以確定的預期,更好地實現定分止爭。經過這么多年的實踐探索,各種問題都有充分的暴露,也有全面深入的討論,在此基礎上求同存異,統一法律適用方向,應該不是難題,關鍵是有權部門要盡快作為。像當年卡拉OK著作權保護、商業標識權利沖突等問題都曾經歷過較大爭議,最后都由最高司法機關一錘定音。
二、如何看待電子游戲的兩種保護路徑選擇
當初將所謂的“換皮游戲”納入反不正當競爭法保護(如早期上海一中院判決的“爐石傳說”案),有不得已而為之的原因,如當時將游戲玩法和規則理所當然地納入思想的范疇,將其排除于著作權保護,但又感到有保護的必要,或者說感覺如不保護就不公平,因而選擇了反不正當競爭法保護,由此開啟了反不正當競爭保護之路。此后,又有感覺可以納入著作權保護的情形或者認識,如將游戲畫面納入類電作品等著作權保護,或者干脆認為高度具體化的規則和玩法逼近規則和表達的臨界點而可以認定為構成表達,而直接以著作權法進行保護。迄今兩種保護路徑始終存在。
我近年來一直主張反不正當競爭法對于新權益有“孵化性”保護的功能,即在新權益有保護的必要,但對于能否納入著作權等專有權保護存在爭議或者一時看不清楚,遂在著作權保護與反不正當競爭之間進行搖擺,反不正當競爭保護通常被作為一種替代性、嘗試性和探索新的路徑。經過一段時期,可以在兩者之間形成一種共識,要么歸入專有權保護,完成了專有權的“孵化”;要么因為實在不能歸入專有權的保護,而最終留在反不正當競爭法保護。能夠歸入專有權保護的,盡量歸入專有權。因為專有權有更為完善的權利框架和清晰的保護邊界,有利于權利保護的確定性;依照反不正當競爭法第2條進行保護畢竟有太大的不確定性。
當前認為電子游戲不能作為作品保護的理由有多種。最為常見的是,囿于思想與表達二分法,將游戲規則和玩法其理所當然地納入思想的范疇而排除于著作權保護。但是,又感到有必要保護有創新性和有較大投入的游戲規則和玩法,所以尋找替代性保護路徑,結果還是給予了保護。其實,著作權法與反不正當競爭法本來應該是協調的,因為公共政策原因不能依據著作權法保護的思想,通常也不予反不正當競爭法保護,否則在公共政策上存在沖突。感覺應當保護而又受思想與表達二分法局限的,更多是因為對于思想與表達的理解有問題。因為,思想與表達二分法在典型的情況下有清晰的界限,但非典型情況下有模糊區(霍姆斯所說的法律的“半影區”)。此時對于思想與表達的區分需要引入價值判斷等,不再是簡單地和機械地加以區分。電子游戲的所謂規則和玩法雖然被稱為“規則”和“玩法”,但實質上或許就是游戲類作品的獨特表達方式,在作公有領域和合并原則等排除之后,可以作為受保護的表達,不一定非要一定歸入思想的范疇。是否納入著作權保護,首先是基于對游戲保護的總體價值判斷而進行的具體路徑選擇,如果總體判斷以作品保護游戲(包括規則和玩法)更為妥當,則所謂的思想與表達就是個法律解釋和操作方法問題,法律適用的細節應當服從于保護需求,而不是保護需求為機械的既有看法所拘束。所以,到了目前這個階段,應當首先判斷哪一種路徑更為符合游戲的保護實際,哪種路徑總體上更具妥當性,給游戲保護做一個宏觀定位,然后再恰當地解讀保護標準,而不是讓游戲保護簡單地削足適履。這是新權益保護的常規路徑和法律方法。
有人認為,游戲的組成部分各有不同,分開保護更有必要。我感覺游戲本身客觀上是一個整體,在整體上考量其法律涵攝而納入一類保護客體,更為符合游戲本身的客觀實際。將其整體納入作品保護,不影響局部侵權(實質性部分侵權)時的侵權行為構成。有人認為,游戲種類太多,不適宜納入著作權保護。雖然游戲的具體類型眾多,但總歸有最為本質的共同特征,畢竟是物以類聚,否則不能歸為游戲了。就像其他作品也有類型繁多的情形,但不影響在統一的作品概念和標準之下進行保護。有人說,游戲更具有競品即市場競爭的商業產品的性質,保護的基點是市場利益或者競爭利益,因而以反不正當競爭法保護更為合適。但是,商品與作品保護并無沖突,軟件等作品都是商品,都可以受著作權法保護。著作權同樣保護市場競爭利益,只是以更為確定的權利化方式保護競爭利益。因此,以商品說或者競爭利益說排除著作權保護很難成立。有人認為,反不正當競爭法保護具有靈活性,更為符合游戲保護的實際,也更利于進行利益平衡。但是,這既是優點又是缺點,通常是不得已而為之。著作權法保護在具有權利確定性的同時,同樣又具有靈活性,同樣可以進行利益平衡和考量產業發展,尤其是通過公有領域、合并原則等確定不保護的內容。
綜上,基于當前游戲保護的實踐基礎,我感覺已具有在宏觀上衡量是以著作權保護還是反不正當競爭保護游戲的利弊得失的客觀條件。在總體上判斷哪種保護模式更為妥當的基礎上,再決定思想與表達等具體的解釋問題。具體問題不應該成為保護的障礙,而應當服務和服從于宏觀判斷。將游戲整體納入著作權保護,并不具有天然的障礙,一切取決于那種保護更合適和總體更有利。
三、如何看待反不正當競爭法保護中的商業道德標準
商業道德是不正當競爭的根本性或者特色性衡量標準,也是反不正當競爭法的基石。反不正當競爭法起源于對于競爭自由的濫用,衡量標準是高貴商人的行為標準,被歸結為商業道德標準。法國、德國初期的反不正當競爭法均采納商業道德標準。但是,競爭行為的正當性畢竟不好判斷,為防止商業道德標準的主觀化,避免對于市場的不適當干預,又始終將商業道德標準客觀化,即以行業內公認的行為標準或者慣例(慣行)進行判斷。保護工業產權巴黎公約采用了“違反工商業慣例”的不正當競爭行為界定方法,也是以既有法德等國家的國內標準為基礎。
我國1993年反不正當競爭法采納了“公認的商業道德”標準,這是傳統的反不正當競爭法標準。2017年法律修訂為“商業道德”,原因是除有公認商業道德的行業外,還有新的領域尚未形成公認的商業道德,需要司法進行創制。最高法院在“馬達慶案”中將商業道德解讀為商業倫理,即特定經營領域的行業或者職業倫理,以區別于世俗道德標準或者高尚道德,實現了“在商言商”的澄清。顯然,我國的商業道德仍然應當是客觀標準,特別是以行業內公認的行為標準為優先標準。即便在新行業需要創制道德標準,也應當將考量因素客觀化。反不正當競爭司法解釋對此已有考量因素的具體指引。以反不正當競爭法保護電子游戲時,同樣需要基于電子游戲領域內的商業道德,即首先是電子游戲行業公認的行為標準,或者在缺乏公認標準時由法院基于法律精神、行業發展需求等創制的道德標準。對此,實踐中已有很好的實踐,值得總結升華。